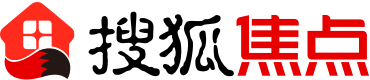乡土中国2016:在城里买房 不会再回到土地
2016-02-17 07:43:43 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

编者按
今年的春运再次刷新人口迁徙的记录,无数人从城市再次流回乡村。得益于互联网,城乡问题的探讨在春节达到沸点。相对于城市而言,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,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。而城市也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,同样面临太多问题。简言之,城市无法拯救乡村,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。我们的编辑记者通过回乡的观察,各自给出了自己在经济增速下滑这一大背景下关于城乡问题的答案。编辑郑升认为,“乡村文明”没有继续丰腴存在的可能。而在记者杨志锦的山村,朴实的村风依然存在。这一组见闻录,只是在这个敏感的改革窗口下管窥一豹,却也更耐人寻味。
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 郑升
来自湖北孝昌县
看了在春节期间刷遍朋友圈的《返乡笔记: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(后面简称《图景》)一文后,始终有如鲠在喉的感觉。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写作时饱含对农村亲人的情感,但并不能认同《图景》作者提出的“回馈乡村”的解决农村问题的说法。
并且,我不认为现在所谓的“乡村文明”有继续丰腴存在的可能。
我的老家就在《图景》一文所提到的湖北省孝昌县,是一个约摸200人的小村子,村里的情况与《图景》一文所描绘的也大体相同。我从小在那里长大,后来经过高考走出村子,但并没有隔断与亲人的联系。
从记事开始,村子就不是文词中“山清水秀”的地方。村里只有两家姓,往上追溯迁徙到这里的时间,祖父说也不过六七代的样子。这样一个不算贫瘠,但也特别不算富饶的地方,养活的总不超过300人。
前几年,村里的耕地承包时间到期,祖父作为村里年纪较大的老者,主持了“分地”再次签订承包合同的过程。那时候我才知道村里的“水田”和“旱地”总共也不到500亩,且超过3/5是不能种水稻的“旱地”,人均也就1.3亩左右。
村里有两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,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深刻:一个是每年春季清明节前后,一个大家族内都会相互帮忙“插秧”;另一个是每年大概在腊月上旬,村里会组织劳力去承包的鱼塘里“起鱼”,然后平分给每家每户。
“插秧”对于以水稻为主食的农民来说,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农时一误,耽误的可能就是一家人一年的主要口粮,因此,一个家族内相互帮忙是沿袭千年的习俗。记得大概是在1992年前后,我排名前列次下水田插秧,当时跟我在同一个水田的大多是自家的叔叔婶婶和姐姐们,叔伯和大哥们则承担运送秧苗和平整水田的工作。
“起鱼”更像是一个盛大的聚会。鱼塘里的水会被抽干,男人们负责下水摸鱼,女人和孩子就提着篮子在旁边看,或者跟着老人们一起七嘴八舌讨论怎么分鱼。最后按照户口数,把摸到的鱼平分成几十份,各自提回家。
现在想来,那应该是我们村人力最富余的阶段,60岁余的祖父辈和30岁余的父亲辈,还都能留在田间地头侍弄庄稼,女人们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田间重活,家里的菜畦与田间的小路还是层次分明的,没有几株野草。
祖父说那时候村里的人口实际比现在还要少些,但是孩子很多。以与我基本同龄段的1980-1990年出生的来计算,能有30来人。很少有人会外出打工,当时少有走出村子的人,应该是祖父的弟弟,70年代村里排名前列个大学生。
1993年,父亲到城镇里做了点小生意,此后村里的面貌在我记忆中飞快变化起来了。先是几乎所有男劳力都跟着远亲一起外出打工了,干的都是泥瓦工的活;后来是村里大量建起了二层的小楼,代替了过去一层的瓦房;再后来是村里原本就不多的田地,有很多都以“退耕还林”的名义种上了柏树、枣树、桃树;再后来,我最近一次在插秧时节回到村里时,除了大伯等几个老农民之外,还在田间劳作的,就只有婶婶那一辈的女人们了。
201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老家时,村里基本是每家每户一栋二层小楼,房子的男女主人在过年前才回家,搓上几天麻将后就又走了,留下年迈的老人带着孙子女。村里的“旱地”基本不复存在了,多了一家占地不小的养鸡场和几排来路不明的砖墙,像是圈地留下的痕迹。
如果抽干农村的那台“城市抽水机”确实存在,我想我是见证了这个过程的,但我想事实并非如此。以30年前村里的土地总量计,村里分到每人名下的田地也不过约1.4亩,在中国经济不断攀升的背景下,这些碎片化的土地基本只能解决村里的温饱问题。
而我看见的村里的出路,并不在土地上,而是在走出农村之后。
在我这个辈分的同村人,也就是1980-1990年出生的30多人中,通过高考这条路走出农村的,大约有6位,这个比例在周围村子中也是较高的,我想应该归功于我的父辈们对教育的迷信。
还有20多人并不是高考的幸存者,我却无法相信他们会回到农村。至少,他们现在生活的重心都是在城市,“老家”对于他们的概念跟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而我也相信,他们最终都会留在城市,不管是北京上海,还是武汉、孝感或者县城,他们总会离开土地。
已经留在城市的同村人当中,有一家是在深圳开工厂的,连带一个家族的青壮年都来到深圳,他们不会回到土地;有在县城开瓷砖店并买了房子的,因为小城开发的火爆,家庭收入并不比我低,他们不会回到土地;还有在其他省份三四线城市做装修的,跟着远亲扎根远方,他们也不会回到土地。
比我小两岁的堂弟,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在出门跟同学一起做了几年装修队后,去年年初回到县城,在二中门前开了一家过桥米线的小店,弟媳和二伯一家都跟着过去帮忙。他说,一年下来收入总共有30万左右,刨去房租还有其他成本,落到手里的有七八万,“比到外面打工划来些”。
堂弟说要是今年做得好,就在县城买房子,把小孩都放在县里上幼儿园。我也相信,他们不会再回到土地。
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,这个村子近三十年来的变迁。它不仅是一段农村逐渐空心的过程,更是一段明晰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镇的迁徙过程。只不过这一过程在最开始是被迫的,到后来却是主动的,并且过程还在不断加速。
而我也相信,这样的过程是必然的,也是必要的。美学意义上的“乡村”从来就不存在,不论是精神面貌,还是实际给人的感观,中国的农村都是粗糙的、杂乱的、无序的,美感只存在于惊鸿一瞥中,并不存在于真实的生活。
所以,我想问题并不在农村,而在城市。我的村人们进城的趋势是不可逆的,我希望他们在城市能找到一片生存空间,更希望他们能得到公平的待遇。如果可能,他们还应该带上用土地置换的资本,这样他们才更有能力在城市安家。